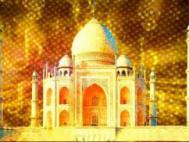帝深疾浮华之士,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阅读答案与翻译-《资治通鉴·魏纪》
散骑常侍作《都官考课法》。然后下诏让百官讨论。司隶校尉崔林说:“好像渔网不能张开,就拎它的纲绳;皮衣毛不整齐,就抖一抖衣领。皋陶在舜的朝中任职,伊尹居于商朝的朝廷,不仁之人,自然远离。考核办法全在于负责考核的人,如果朝中大臣都能胜任其职,作为百官的榜样,那谁敢不好好干,又何须考核!”黄门侍郎杜恕说:“要让州郡官员考察士人,必须经由四个科目(儒经、文吏、孝悌、从政)来考察,如果所说的都有事迹证明,再举荐他,由公府征召,派去做跟百姓直接接触的地方首长。之后再根据他们的功劳,依次补升为郡守,或者官职不变,只增加俸禄并赐给爵位,这才是最重要的考绩。至于公卿及宫中内职大臣,也应该进行岗位考核。况且天下之大,事务繁杂,不是一盏明灯就能全部照亮每个角落的。所以君王为元首,臣子为股肱,君臣一体,相辅相成。所以古人说,廊庙栋梁之材,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的;帝王之业,也不能靠一个人的谋略。由此说来,岂有身为大臣,成天在那里办理考核,就能让天下太平的呢!”司空掾、北地人傅嘏说:“建立官吏,分担职务,管理民众事务,这是根本。而按照他的官职去考核他的实际工作,根据成规去考察督促,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。纲本未举,而去制定一些细枝末节的流程;不研究经国大略,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。我担心这并不足以分辨官吏的贤愚,也不能精进孰明孰暗的道理。”讨论来讨论去,很长时间都没有结论,考核之事终究不了了之。
司马光说:“为治之要,莫先于用人。而治人之道,就是圣贤也觉得困难!所以,如果按舆论对他的毁誉去选拔,则被喜爱和憎恶所主导,而善恶混淆不清;按考核条例去检查呢,又巧诈横生,真伪难辨。总之,根本还是在于人要至公至明罢了。在上位者至公至明,则群下能否胜任一目了然,无所逃遁。如果在上位者不是至公至明,那考核办法,恰恰是被利用为徇私欺罔的工具。

 实用的生活知识参考!
实用的生活知识参考!